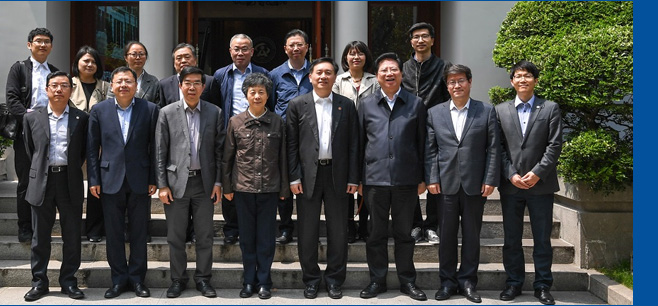彭勃 | 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Release time:2020-06-17 11:08:00
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彭 勃
作者彭勃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论文原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摘 要:作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工具,技术治理的绩效在不同类型治理领域中存在较大差异。技术治理以信息量化、清晰预算和精细管理等工作机制,明显提升了行政体系在传统优势领域即小规模诊疗型治理中的能力。由于技术治理自身不能突破行政机构的内在缺陷,尤其是在行政体系传统弱势领域即大规模预防型治理事务中,并不能有效推进治理现代化。技术治理本身并不自带现代化属性,要推动治理现代化,必须抛弃技术治理自我合法化的谬误,并充分认识技术治理的内在缺陷和功能弱点。应当运用技术治理的手段,弥补行政科层制内在缺陷和功能弱势。技术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寻求技术穿透社会的制度支撑,弥补政府治理缝隙,解决委托-代理难题,以及应对现代治理日益加剧的复杂性问题。
关键词:技术治理;治理现代化;治理绩效
文章节选: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现代科技手段越来越受到青睐。不论在最高层的政策文本中,还是在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创新实践中,通过技术治理的路径实现治理现代化,已然成为共识和共同的趋势。各级政府不惜花费巨资推动科技赋能,寄希望于各类科技手段,为公共治理插上技术的翅膀,技术治理被看作是通向治理现代化的坦途。诚然,技术治理自带“现代化”的光环,在现实中也不乏技术治理实质性提升政府能力的案例。但是,在理论逻辑上,技术治理与治理现代化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在技术治理的名义下,也发生了明显的治理偏差,与治理现代化背道而驰。针对这些背景,本文将讨论技术治理的本质和工作机理、技术治理的强项与短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治理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治理。
一、技术治理的实质
技术治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当人类将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运用于公共治理时,技术治理就成为公共治理的模式之一。技术治理的内涵涉及运用于治理实践的各类技术,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技术治理的核心内涵与关键元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哲学和认识论层面的技术治理。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定义非常典型,他认为技术是让事物的状态从“潜在”转变为“实在”。无数“潜在”的可能性,一旦被技术转化为“实在”,其他可能性就被限定,事物得以显露意义。可以说,技术是人类运用理性来认识事物的工具和手段。
第二,作为工具和方法的技术治理。运用技术方法增强治理能力,是现代官僚组织理性精神的重要特征。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的理性主义精神建立在严格的簿记和核算之上,而基于理性主义精神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其行政管理优越性的强大手段是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的不可或缺性是受商品生产的现代技术和经济制约的……除了财政上的前提外,对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还存在着十分重要的流通技术,行政管理的精确细致需要有铁路、电话、电报。在专门的知识之外,官僚体制还倾向于通过公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其权力,在公务交往中获得“熟谙档案的”实践知识。
第三,作为权力工具的技术治理。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建立在相应的技术之上,通讯和信息储存技术的提升,强化了行政力量监控社会的实际能力。福柯则强调知识与权力的运作,包括现代国家的区分技术与规训技术的运用,以及人口技术和生命政治的关系,并以此讨论国家的支配技术。在福柯看来,国家的治理术是用技术构成框架而塑造人的行为,其原理是一整套制度、程序、计算、分析组装起来,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类型,以安全配置为工具的一系列复杂的权力运作。
进入近现代以来,国家的职能不断扩张。面对越来越多的治理任务,传统的民主问责和有限政府模式无法满足要求。现代科技知识所支撑起来的技术手段,成为弥补治理能力缺口和解决复杂难题的顺手工具。相应地,对于技术的崇拜和技术乐观主义达到高潮,运用技术治理达成理想社会的“技术乌托邦”思想也开始出现。然而,技术治理这个武器并非攻无不克、无懈可击。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和模式,技术治理一直面对技术失效的困顿,技术治理也引发了相关的负面问题。
第一,工具理性的误区。技术治理秉承了工具理性的核心内涵。偏执于技术理性和对价值理性的忽略,使其面临治理困境。由于认识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限制,又受到组织、社会、情感等方面的干扰,单一的工具理性路径必然存在偏颇和缺陷。工具理性的局限性折射到技术治理模式上,即为了自我证明技术治理的有效性,不断复制和强化技术手段,并以各种应对策略和折衷办法,弥补技术治理产生的负面效应。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凸显其治理弊端。工具理性所催生的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造成一系列治理弊端,过度的简约治理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简约主义的谬误。问题本身是潜在的,也是模糊而复杂的。在运用这些数字、符号和指标指代时,必然发生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模糊的问题清晰化。只有这样,潜在而复杂的问题才能被感知和理解,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简约主义。对问题的裁剪和简约处理,势必产生信息丢失、扭曲与偏离现象。这种技术治理思维导致的简单粗暴的简约治理方式,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本身就成为产生问题的根源。例如,为了提高林业收益而将天然复杂的森林生态简化为单一的树种;将坦桑尼亚自然的村落按照几何原则进行武断的规划改造,终使国家宏大的社会改造项目归于失败;将历史积淀形成的都市街区,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进行重新规划,并建造机动车道路,最终扼杀了都市活力和生机。同样的例子,一些地方将扶贫工作简化为盖新房子,将农村社会发展简化为新式厕所,将城市社会生态简化为街面违章违规建筑的拆改等。
第三,权力的侵入和操纵。技术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的主体决定了工具的性质和使用效果。在技术治理的过程中,渗透了工具使用者的权力意志。技术治理的理想状态是专家治国,秉持科学管理精神,实现所谓科学的乌托邦。但是,技术治理运行中始终渗透着官僚理性。被推崇备至的纯粹中立的技术治理,常常被权力扭曲和利用。信息和数据本身没有立场和观点,技术的立场和叙事方式,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权力的意志。因此,技术治理的实践也存在立场和方向。在当前技术治理推动的治理创新中,技术工具掌握在上级政府和强势职能部门手中,技术治理的科学叙事背后,往往渗透着权力的意图。可以说,政府希望通过技术治理来实现超然、客观和中立的治理目标,而国家通过技术治理的窗口,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背影。
第四,制度和组织的限制。尽管有不少人迷信所谓技术的刚性,认为技术可以超越制度界限,冲破组织壁垒,只要技术一旦被采用,就能够自发地发挥结构性系统重组的治理效能。但是,现实中的技术治理不是天马行空、往来于真空当中。它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施展,需要在一定的组织条件下,才能运用到治理过程中。制度和组织条件是影响技术治理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当前,技术治理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合治理机器、提高监控能力的功能,但是,技术要充分嵌入治理过程中,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和受制于制度安排。如果规束权力关系的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依然发挥作用,就会对技术治理的效果构成很大的影响甚至是阻碍作用。更进一步,技术治理本身被有目的地设计和采用,技术治理被制度型塑和改造的情况在基层治理创新中比较普遍。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6-107页。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8页。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8-250页。
4.[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4页。
5. 转引自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社会》2018年第3期。
6.[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
7.[美]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8. 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社会》2018年第3期。
9. 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以上海市 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社会》2010年第4期。
更多精彩内容请阅读原文: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_治理现代化的视角_彭勃.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