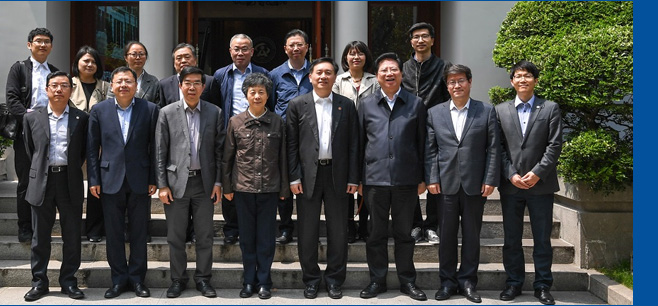【治理现代化】姚尚建 |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Release time:2020-07-07 14:56:00
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姚尚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围绕“城市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改革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协办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专题研讨会于5月30日在线上召开。日前,研究院编辑整理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形成观点,在公众号和网站陆续分享。本文为第六篇。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城市治理的区域扩散: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按照初步的思考,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报告。我们先谈结论,在中国整个的治理过程之中,城乡合治和城乡分治是不固定的,从而赋予城市治理和区域治理以不同的任务。西柏坡会议关于生产性城市的定位,给中国城市的治理和城乡关系,乃至区域治理提供了纲领性文件。后来的城市治理在很长时间里面,是对西柏坡会议精神的确认和发展。下面从四个方面进行报告:
第一,生产型城市治理的优先性;
第二,市领导县与市域治理的形成;
第三,市域治理现代化及其扩散;
第四,城市权利的区域达成。
01 生产型城市治理的优先性
在西柏坡会议,毛泽东主席有这样的判断:我们要建设生产型城市而非消费型城市,这和人民政权的关系是高度相连的。毛主席也同时确定了中国城乡关系,即不能光顾城市而丢掉乡村,这个判断在很长时间里面指引着我们国家城市治理、乡村建设乃至区域发展。在这样一个定位中,毛主席要求全党要一步一步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国营工业,第二私营工业,第三手工业。毛泽东主席强调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人民政权才能确定。同时毛泽东主席对整个中国城乡面貌还是非常担心的,他说中国已经有9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和古代是不同的;但是中国还有大概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区别。
工人阶级领导城市生产,工业化领导城市化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实践。一五期间,苏联援建并投入使用的150个项目对中国的中西部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我国也有过一段时期的三线建设,客观上也形成了攀枝花、六盘水等一批工业城市。当然由于多数三线工厂本身是封闭的,因此很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由于这些工厂很多本身就是从大型城市里面搬过去的,所以损害了既有的城市产业体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确定了工业化领导城市化的基本思路。基于生产型城市的建设,我们确定了城市优先的原则,票证、户籍、统购统销三个制度锁定了城市公共服务,锁定了城市居民的优先权利。
02 市领导县与市域治理的形成
在城市优先发展过程之中,北京、天津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市领导县,那时候被市领导的县数量不是很多,被领导的县是城市的米袋子和菜篮子。不领导县的城市也有自身的菜篮子和米袋子,我们谈到上海就有全国最大的一批飞地如大丰农场、梅山铁矿、安徽的黄山林场等。1958年,随着整个松江专区从江苏省转给上海市,上海市也确立了市领导县体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从江苏、辽宁开始,市领导县体制全面铺开,意味着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的开始,意味着城乡互动的深化。随着以市域为单位的整个的空间发展,城乡融合、互通、互动在这个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
03 市域治理现代化及其扩散
市领导县还意味着城市制度的区域扩散。为了促进这一时期的区域发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务院同时启动了上海经济区建设,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放在上海,不久这一尝试就失败了。但上海经济区失败以后,长三角的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却成功建立起来,为什么会成功?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视角的差异,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问题在于把城市理解为区域治理的一部分了,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功,则在于把区域治理视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之下,整个长三角区域版图逐渐扩张,我有一个学生在做注意力分配的时候发现,随着长三角规模的扩张,安徽省政府的注意力越来越聚焦于长三角一体化,这种越是边缘地区越向长三角注意力集中的态势,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随着整个城市空间的扩张,市域治理的制度持续推进,不仅仅形成城乡空间的融合,也逐步溢出了市域的行政边界。在面对整个跨域问题的时候,传统的治理方式偏好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外部问题内部化。行政区划作为一个行政手段解决跨域问题的时候,肯定存在很多不足,我们要突破这个外部问题内部化的思维定势,要主动把很多区域的问题理解为城市的问题,通过资源共享淡化行政边界。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例如洋山港的管辖问题,上海新机场的选址问题,苏州和无锡机场共享问题,所以我们要讨论如何突破行政边界,让共享资源得到制度性的确认。
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市域治理先进制度的扩散,市域治理还需要技术的扩散。我们对于城市和区域关系的认识会影响我们的政策选择。我们在整个技术治理过程当中做到哪一步了?在疫情时期,我们推出扫码治理,但是这种扫码不能是“一城扫一码,一码归一码”。上海一度宣布苏州是疫区,苏州人到上海就要隔离,但是昆山花桥那一带,有很多工人是跨境上班的,他怎么隔离呢?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后来为了方便企业员工的跨省通行,嘉定和昆山签定了联防联控备忘录,相关员工持证件进出两地。上海市金山区和浙江省平湖市、嘉善县也推出了三地车辆互认通行机制,解决了疫情期间的交通互通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上海在这个时期关于跨域治理问题处理得比较早,让健康码的问题首先得到了跨省的互认,这也说明即使在非常态的治理过程当中,技术也是可以区域扩散的。因此制度与技术的扩散使我们在长三角示范区里面可以突破边缘的弱化,防止长三角示范区和先行区里面交叉地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死角,不断提高边缘地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04 城市权利的区域达成
梅因说过,所有社会进步的进程,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按照列斐伏尔的判断,人口流动是为了实现城市权利。对于城市来说,城市权利的实现是城市治理的核心。城市权利如何从哲学问题变成法学问题,如何从法学问题变成政策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解释的。大家看到在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里面,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规定,例如探索城市群的户籍通迁,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我们要重视这样的变化,我们搞超大城市的控制人口解决不了流动的问题,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分配面临很多的不足,尤其是个人口随迁和服务的问题,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变化。
如果说在传统中国,县域社会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体系,具有连接基层社会与整体社会的功能,那么在新形势下,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借助于技术与制度的扩散,市域已经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个新的治理节点。在此基础上,市域治理也将形成区域治理新的基础。因此,我们要重新反思城市治理与区域治理的关系。以往的治理由于市—县—乡等复杂的政府结构,习惯于把城市问题理解为区域问题,把市域治理理解为区域治理,甚至一度导致同一城市内部治理脱节,其中上海市不同区的断头路长期无法打通就属于这样的典型。市域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主动把本辖区甚至跨域问题理解为城市问题,把辖区和跨域治理理解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城市权利的区域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