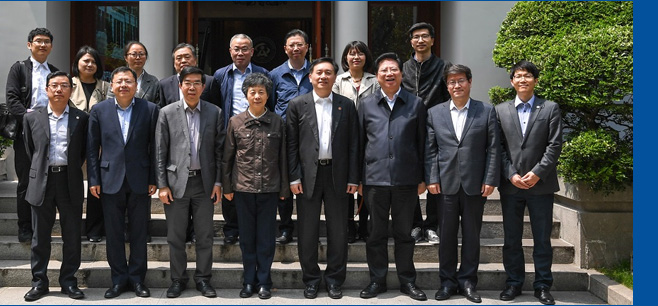陈杰:【人民论坛】中国治理现代化要跨越“现代性”陷阱
Release time:2019-10-31 14:12:00
作者陈杰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摘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做更深入的理论理解。本文从治理语境中的“现代化”与世界观意义中“现代性”的区别及关联入手,既指出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中国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哲学与技术支撑,也提出要防止中国治理现代化建设陷入基于西方现代化实践的“现代性”陷阱,走出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价值的治理现代化建设之路,并总结出一套具有广泛参考价值的国家治理模式,从而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现代化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C19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治理现代化成为中国治理领域的重大理论构成。学界和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治理现代化是党和政府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农业、工业、国防与科技领域实现“四个现代化”、2005年“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内涵的“新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总体战略发展目标之后,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新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然而,除去学者们围绕“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广泛讨论外,关于到底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和基本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理论讨论还不够充分。更为突出的是,治理语境中所说的“现代化”到底是什么,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意义上的“现代性”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理论讨论更是稀少。这直接让治理现代化的指向缺乏足够的清晰性,进而带来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模糊、治理现代化的道路缺乏指南等问题。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为更好迎接新一轮对治理现代化的大讨论,本文对治理语境中的“现代化”一词进行重新考察,试图从治理语境中的“现代化”与世界观意义中“现代性”的区别及关联入手,既指出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哲学与技术支撑,也提出要防止治理现代化建设陷入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现代性”陷阱,走出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价值的治理现代化建设之路,并对已经走过的治理道路加强总结提炼,对已经取得的治理经验进行更高的理论提升,上升到具有普适性和广泛参考价值的国家治理模式,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现有文献对治理现代化的理解
学者们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维度和衡量指标提出了很多见解。俞可平认为,衡量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考察: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俞可平,2014)。此外,他还进一步提出,现代化的特征就是标准化,为此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就是标准化(俞可平,2015)。何增科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包括四条:民主化、合法化、文明化、科学化(何增科,2014)。薄贵利认为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分权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薄贵利,2014)。徐勇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评价指标包括: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协调化与高效化(徐勇、吕楠,2014)。张文显提出,考虑到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张文显,2014)。
这些论述为理解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出发点,而且存在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很强调民主化和法治化,也很关注科学性和效率性。不过,这些论述或多或少将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或治理技术的现代化有所混淆。治理现代化,首先是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其次是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治理技术的现代化。此外,这些论述都是基于经验概括上的列举,没有从本质特征上回答,为什么所提出的那些内涵和指标代表了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论述都没有从哲学反思层面说明,为什么“现代化”就是好的,换言之,为什么需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因此,讨论治理现代化的现有文献中对“现代化”本身的理论阐述是不够的,既没有提出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也没有说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现代化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已有一些学者力图将治理现代化建立在现代性概念的基石之上。如认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指治理能力具有现代性特征并符合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的一种状态”(李文彬、陈晓运,2015)。但该文没有对现代性及现代性特征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影响和约束治理现代化做进一步讨论。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实践要超越基于异化逻辑的现代性治理技术,建立在人民逻辑上(张丽、朱春艳,2018)。但文章没有进一步讨论文中所指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关系。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别与联系
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别与联系,一个广为引用的观点是,“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布莱克,1989)。在这个表述中,现代性是相对静止的一组特征,现代化则是面向现代性逼近的动态过程,或说“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近现代以来,面对民族存亡巨大危机的中国知识界很早就开始热烈讨论现代化命题。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提法。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概念及命题的认可和热衷,具有压力下的被迫自我反省的特点,“表明人们开始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明之关系,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朝上国’这样一种‘天下观’的束缚,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从而也就承认并强调‘现代化’的必要性”(邹平林、杜早华,2012)。但也对现代化的理解带有片面和肤浅的一面,往往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罗荣渠,2008)。
只有在中国真正迈入现代化进程之后,中国学者们才开始探究现代化的内涵,并意识到必须与现代性的讨论联系起来。基于对前人观点的总结,笔者认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属性,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提炼、总结与结晶,又反过来不断影响和刻画新的现代化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既是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又是现代化结果的产物,进而影响未来的现代化。
“现代性”的陷阱
然而,一旦进入到对“现代性”的探究层面,就会发现无论是“现代性”概念还是“现代化”概念,都存在很强大的陷阱。这些陷阱隐藏很深,暗含了种种让人很难发觉的迷思。
首先,“现代性”或“现代化”都暗含假定:新的比旧的好。“现代性”具有很强的时间维度和历史维度,“现代性是一种自觉与传统决裂的时代观念,同时又是变动的时间意识”(王晓林,2006)。在直线矢量的时间观与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结合下,“内在地蕴含着被思潮化的达尔文主义关于时间与历史矢量进步主义的立场”(尤西林,2003)。作为现代化过程的特征凝集,现代性不仅直接与自然性、原始性相对,还与“前现代性”相对。现代性的概念内生了一种语言霸权,一切“前现代性”都被其贬低。如吉登斯把“现代性”界定为“后传统的秩序”。
其次,“现代性”或“现代化”暗含假定趋同,否定多样性,即存在一个或一群标杆式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别的国家与别的社会形态都务必向其看齐,除此之外不应有其他选择。“现代性作为理论形态的现代社会自我意识,是对现代社会整体状况的哲学表征”(周丹,2013)。但在实践中,由于“现代性”往往就是被定义为那些在科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本质特征,“现代化”则自然而然就要求传统社会、落后社会向先进社会靠拢与趋同、从先进社会获得其特征(布莱克,1989;陈嘉明,2003)。而最先进的标准往往只有一个,排斥其他标准的存在。
第三,“现代性”的定义往往被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所垄断。由于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保持科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领先优势,“现代性”默认成了西方性,“现代化”默认成了西方化。“一方面,西方文明的崛起将世界上其他处于传统社会的民族国家强行拖入全球范围的现代性进程,另一方面,这种进程又迫使后发国家将追逐西方化作为自身发展的一个目标”(郭大为,2004)。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标杆形象的塑造过程,不仅基于国家实力的反映,也是一种话语权力量对比的结果,体现了文化霸权的输出。比如,二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崛起的经验,其实已经打破了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传统定论,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东亚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不同(金耀基,1996),但东亚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的总体弱势,未能改写西方老牌发达国家对“现代性”内涵的垄断。向西方模式的现代性进军,仍然被广泛认为是一切后来国家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
第四,“现代性”还制造了一个人们难以察觉的迷思,即作为标杆的“现代化”国家的一切都比“非现代化”国家好。尽管现代性被定义为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韩庆祥,2016;王晓林,2006),但在现实实践中,哪些是根本特征,哪些是非本质特征,很难辨识。因此,一旦落后国家开始向标杆国家学习,往往会盲目学习标杆国家的一切。“西化”演化为“全盘西化”。从概念本身而言,何为“现代”,何为“前现代”,何为“后现代”,本身应该天然动态演进、与时俱进、日日更新。然而,在现实任何一个时点上,现代性所体现的制度机制、法律法规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不可能随时变化。而制度往往都有很强烈的“路径依赖”,甚至有“锁定效应”。所以今天在标杆国家所观察到的很多现代性,其实都是这些国家“前现代”时期留下的历史遗迹。比如英国、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至今保留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的制度安排,就不具有现代性,仅仅是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传承。然而,在后发国家眼里,由于没有经历相同的现代化过程,无法分辨“现代社会”的特征中哪些是现代性、哪些是前现代性,往往会造成对标杆国家的盲从。
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性特征、驱动力和缺陷
对中国乃至其他后发国家而言,现代性都是一个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舶来概念。在制度维度上,西方现代性具有理性化和精密化特征。韦伯认为,理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内核,现代化就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为此“理性化”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化的标志性特征。
沿着这个维度,现代性被解读为“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具体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衣俊卿,2004)。治理本身就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为此西方的治理或公共行政显示出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公共行政领域的现代性则主要表现为技术主义、科学主义、专业主义和企业逻辑四大特征”(刘耀东、孟菊香,2018)。
但西方现代化过程又是怎么起源的?西方现代性又是如何获取和被塑造的?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逻辑,是西方现代性的起源(丰子义,200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动态的运动,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是无限制地增殖、膨胀。表面上看,资本运动的逻辑基于资本家追求财富的无限欲望,但资本家也可以看作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可以说那些有意愿也有能力去满足资本运动逻辑的人才是资本家。“马克思的上述见解蕴含着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即资本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也构成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俞吾金,2005)。基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可以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是资本运动逻辑的产物,来源于“生活世界的货币化”(鲁品越、骆祖望, 2005)。根据这个理解,理性化、分层化、个体化和非人格的法治化等现代性或西方现代化社会的显著特征,说到底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
但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资本增殖驱动的现代性,存在诸多悖论,如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积累增加与扩大再生产所需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积累——消费悖论”。所以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总是带有种种激烈的社会冲突,突出的如生产过剩而带来的经济危机,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对人类精神生活和存在价值的侵蚀,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可统称之为“现代性危机”。基于西方现代化实践的现代性绝不是人类无可挑剔的“至上理性”,它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虚、生态的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王晓林, 2006)。“现代性以及由现代性所标识的现代化运动本身存在着价值合理性危机”,折射到治理领域,西方同样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张雅勤,2015),其背后都是资本诸多悖论的产物。西方社会所出现的后现代性浪潮或“二次现代性”呼声,都反映了人们对资本驱动下的现代性认识的不足,并尝试修补(张雅勤,2015)。
中国治理现代化吸收了西方的现代性但正在超越西方的现代性
西方现代化过程所产出的理性精神、民主、法治、分权、个体独立等现代性产物,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结晶,对中国发展生产力、摆脱传统落后制度走向更高发展水平的文明具有重要作用。但西方基于资本增殖逻辑所驱动的现代性,并不一定是唯一的现代性。朝向西方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也不一定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由此,治理现代化肯定不是只有西方模式的治理现代化这一条道路。西方治理理论已经在努力吸收后现代性理念来弥补传统现代性的缺陷,以避免现代性危机再爆发(刘耀东、孟菊香, 2018)。
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经历了资本运动逻辑和劳动解放逻辑相互博弈相互运动的过程(周丹,2013)。中国的崛起需要借鉴全人类的文明精华,包括各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与启示,但最终需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起中枢作用、最重要的“现代化”,既要承担起承接西方舶来的现代性、融合西方现代性的历史重任,更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陷阱、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自己价值观的现代性的历史重任。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这次讲话,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树立了根本原则。然而,分辨出到底哪些是西方化的治理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的治理现代化,哪些不是,以及哪些是人类可共通共享的治理现代化经验,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积累,在各种实践经验上进行理论升华。已经很清晰的是,中国治理现代化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要扎根中国自身的历史土壤和时代实践。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道路,很多做法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也行之有效。
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多年来中国构建并逐步完善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权力统合制度、以政治民主协商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参与制度、中央统一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国家构成制度、垂直管理和地方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央地分工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机关监察有机统一的治理权力监察制度、基于绩效和测评有机结合的治理人才晋升选拨制度等。在国家治理理念层面,不断与时俱进,在各个时期顺应发展需要和人民福祉需求,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都是对全人类治理思想与经验的扩展、丰富与发展。
党和政府也不断主动推动“放管服”改革,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断重新定义和调整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与普通民众在国家治理中各自的角色与相互关系。越来越强调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水平,并要求以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政府工作的评价标准,“一站式服务”“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等口号的提出与落实,实实在在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都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
在微观层面的社会治理方面,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一直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构建以党建引领的多元共治作为社会治理基础结构的前提下,不仅重在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也强调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方向下,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一直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强调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人民调解员、网格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和网格员等制度的设立,都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独有,并还在逐步完善。
在城市治理领域,越来越多的城市对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的职能进行重新界定,取消经济功能而全面转向公共服务,并全面推动基层政府探索以精细化和无缝隙为特征的城市治理模式。在社区治理层面,各地都在探索推进“三驾马车”(即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分工明确、加强协同、产生合力,努力实现社区有序有活力,基层治理无死角。
可以认为,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建设中既有很强的世界性,又已经体现出诸多中国特色。具体而言,一方面积极引入社会协商、去中心化等后现代性理念思维,一方面坚持从自身国情出发、传承文化历史传统、扎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实践,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等层面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实践新做法,也提出了诸多新价值观新理念新思想,这些都是对西方现代性思维的超越,是对世界意义上现代性的完善,也进而展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中国道路。
结语
2019年9月24日,在主持以“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总结70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要在充分吸收人类共通共享的治理成果精华但防止陷入西方式“现代性陷阱”的基础上,牢牢扎根中国自己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承,走出适应中国需求、符合中国价值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并在中国治理实践基础上,发展出中国自己的一整套治理现代化标准,进而提炼升华形成对后发国家具有广泛参考价值的治理现代化理论,从而在理论上为推动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参考,并在技术上做出引导。
【本文研究工作受NSFC-ESRC联合基金(NSF7166113700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71573166、NSF71974125)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薄贵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2]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4]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郭大为:《现代性的普适性及其风险》,《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6]韩庆祥:《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7]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8]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9]李文彬、陈晓运:《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5期。
[10]刘耀东、孟菊香:《当前中国行政改革中的现代性:构建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9期。
[11]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2]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13]王晓林:《现代化不能拒斥现代性——兼论应对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14]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5]徐勇、吕楠:《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16]杨光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7]杨震:《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认同——以现代性为分析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18]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9]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20]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21]俞可平:《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人民论坛》,2015年第31期。
[22]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3]张丽、朱春艳:《现代性视域中治理术的技术化批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0期。
[24]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25]张雅勤:《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基于现代性分化与融合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0期。
[26]周丹:《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化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27]邹平林、杜早华:《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5期。